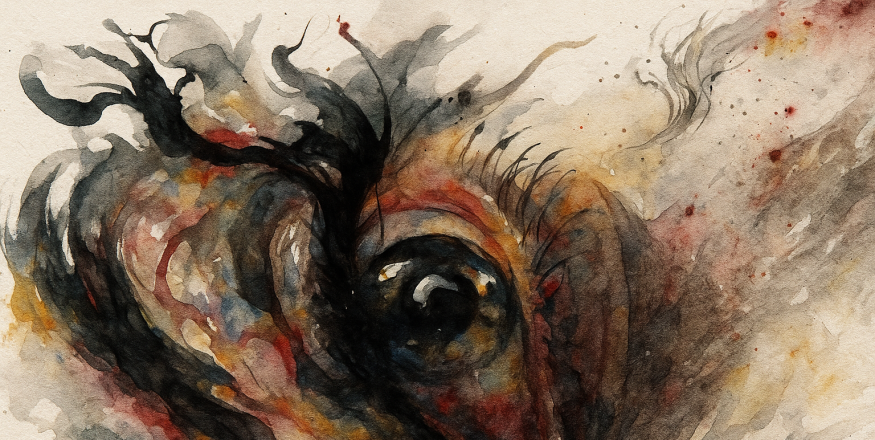他是一個衍生出來的人。他生長在凹陷下去的童年裏,存活在畸形的家庭中,沒有人格,沒有氣力,沒有坐過飛機,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個玩具,他支付不了任何東西,他的家庭支付不了任何東西。考上大學後,他說爸爸,我已經長大了,我想坐飛機去學校,父親好冷峻,說長大和他坐不起飛機沒有任何關係,他睜開血紅的眼睛,所有實體都消溶了。後來按照父親的意願,他鑽研了四年法學,畢業後在城中村裏租下個根本供不起房租的單間,法考是一座跨不過的大山,即便把轉了九手的培訓視頻看了一百遍,即便一直做題,一直做,一直他媽的做,以至於臀部的皮膚連接椅子,成為一樽完美的布藝品,他仍然落敗於三戰。自那以後,他不再有心情備考,轉而用閱讀大量刑事宗卷,尤其是冤假錯案來打發時間,無證抓人,刑訊逼供,死刑之後真凶現身,案情高度同質化,像套公式批量寫出來的一樣,它們給他帶來不安,惶恐,被害妄想,他開始害怕與他對窗的那個老煙鬼某天把煙頭丟下去,在路人臉上灼一道疤,然後員警興致沖沖地給他戴上手銬,他沒想過這樣的閱讀極具成癮性,沒日沒夜地,他看了好多好多,從近兩個月,上到六十年代,當然,如果期望從中悟出些什麼,但凡有一絲這樣的想法都是可笑的。對法律的質疑自這裏開始的話,未免過於俗套了,可終局就是如此,滔天的恨意早晚要來。法律像跑車裏的減震支架,這個比喻是哪個傻瓜說的,他記不起來了,研究惡法還是做點實際的,這很重要。
他每天總是很早醒來,困乏卻又睡不著,坐在電腦前打瞌睡,滿臉倦淚地趴在桌上,像個上班族似的,卻又沒在上班。他的腰被萬丈壓抑塑形,坐姿不定,酸痛難耐,他在辦公,卻又什麼也沒辦,他看著窗外發呆,看著桌上的木紋發呆,看著床頭櫃的止痛藥發呆。冰箱裏是十天前準備連做好幾天飯而買來的、如今已敗爛的菜,同它們一樣,房間裏所有物質都處於失管狀態,像是沒有人居住,他封閉了很久很久,兩眼無神,無法發揮出活人的效益。初醒之時,在床上或躺或坐,他的大腦預演接下來要做的事情,關空調,掃地,下樓買個什麼,悉數算畢,他耗光了所有能量,在完全醒來之前又睡回去。我不是無所事事——他慰藉自己——我是被逼成這樣的。殺保護動物的量刑比殺人重,寫色情小說的量刑比強姦重,他捧著法考的教材,哭喘著自語,爸,媽,我不想為這些東西辯護,我想要公義,我不想當公務員,幾百萬字的狗屎不如一顆子彈方便,你們看,掌權的人不會關心法典裏有什麼。爸,媽,我好難活。爸,媽,大概十年前你們開了家雜貨店,你們把鑰匙扣掛在店門口賣,來了一車城管,說你們占道經營,把媽媽踹骨折了,賠了兩千,後患卻跟了媽媽一生,你們忘了嗎?你們為什麼還要我融進這個邪惡體系呢?你們的思想有處理過前因嗎?你們有認真對待自己的尊嚴嗎?你們強迫我形成胚胎的時候,有沒有提前解析過這場出生呢?你們到底抱著什麼樣的思想帶我來到這個骯髒的巢穴,你們是什麼?你們是誰的信徒?爸,媽,我得了鼻炎,我呼吸不了了,我那樣疼痛,那樣失敗,你們企望的音訊不過是空冥國度裏的一聲失落的歎息,爸,媽。時間的尺度變化成未知的模樣,頻繁食用廉價外賣的果報降臨,他行為舉止總是受酸脹的壓腹感支配,這樣的情形讓他覺得自己的腸子是一鍋肉糜,他居住的這棟樓房,和周遭如同複製出來一般的公寓樓,緊貼在一起沒有縫隙,遠看大片大片的,猶如繁華都市裏生長出的爛瘡,要說蟲豸蛀穿了它們,不如說它們為蟲豸而生,這裏的人謾罵彼此,悉悉索索地偷生,比如有天晚上,大概是前兩天,樓上的女人悲憫地哭嚎,聽上去要淹掉整座城市,後半夜剁肉的聲音又使他心煩意亂,他從一開始就猜到某個人在分屍。分吧,分吧,嗯,他想道,要是我的怨氣無處發洩,我也要切個人玩玩。這一幢幢臭氣熏天的乳酪裏,吵個架像吃飯喝水一樣常見,員警老來這裏帶走一些雞巴人,他們大多就是抬頭不見低頭見的鄰居,愛把啤酒瓶往人頭上招呼的狗操的鄰居,他們用來自五湖四海的口音說著最下流的話,誰打擾誰睡覺,誰收了誰的被子,這不得用鋼筋打瞎一只眼才解氣。後來樓板的縫隙開始漏血水,他睡覺時候頭朝的那面牆,血分成三段支流向下侵蝕,他打開窗,讓風吹幹它,讓它看起來像一顆倒栽的樹,再後來員警找他問了些無關緊要的問題,整棟樓的人聚集起來要上去看看,但員警貼了封條,只有他例外,他被帶到案發地點,兩房一廳,外加一個狹窄的小廚房,裏面有個刑警揮刀砍砧板,問他是這個聲音嗎。
“是。”
多少天了?
“什麼?”
他從幾號開始剁屍體的,剁到了幾號才消停?
“記不清了。”他說,“我都記不清自己活了多久。”
員警們叉腰杵著,並不輕鬆地研討案情,他站在客廳裏,瞟向半掩著的臥室,門縫大概十指併攏那麼寬,床邊有個油桶,吸頂燈和陽光把它照出兩個影子,女人蹲在桶裏,沒有四肢但高昂著頭,兩個眼洞插著破碎的啤酒瓶。油桶上被人用記號筆劃了很多符號,像順時針轉九十度的“Ω”,不過上下兩條尾巴長許多。兇殺案導致至少三分之一的租客離開,但他沒有,他帶著鼻炎在這個房間裏度過了整個夏天,也正是這個夏天之後,又發生了一些事,以至於他愈來愈不信任自己。
他說:“那麼……實際上,我生活的社會是個大型垃圾場,包括我在內的所有低產者都是垃圾,現在我想起來了,大概兩周前的事,在我看來像兩小時前發生的,時間過得太快,死人都沒人討論了。我遲鈍,我後知後覺,這怪得了我麼?你可以把這個當作一個倒裝的解釋,以免我說完後被你立刻質疑。血水滲透下來的情況,說明這棟樓的品質相當低劣,我突然想起以前吃過好多虧,有一次房東鋸掉我的窗臺,我失去晾衣服的地方——不是曬,是晾,因為我的房間沒有光——我說這等同於減少我的居住面積,面積減少意味著房租減少,他說這不關他的事,是區裏面不讓房子凸出來,說話的時候他笑得無比輕鬆,當我再次要求減房租時,他連看都沒看我一眼,只是譏笑一聲,說你做什麼美夢,轉而與別的租客攀談。樓上的女人死掉後,有東西點通了我的思想,我是學法律的,我要跟他鬥一鬥,把舊賬翻出來的話,太遲不說,還顯得我怯懦,那我也跟他說我要搬走,搬走的理由毫無疑問,這他媽是個凶宅,說宅還高看它了,凶間差不多!儘管我並不在意死沒死人……我是學法律的,我應當這樣催眠自己,我是個對死亡司空見慣的大律師,我操,我是個大律師,那麼流程便這樣開始了——我得搬走,收回押金,再提起滲血的樓板要精神損失費,這尚且不夠,再提起被鋸掉的窗臺要民事補償。我過分嗎?看起來是的,可與他的所作所為相比根本不算什麼,那利慾薰心的狗,同其他利慾薰心的狗一樣,仗著自己在一塊靠近地鐵的好地勢上有棟公寓樓,草草裝修一番,極似地下室的陰濕環境,哪怕區區十平米也能租一千出去,長久以來我活在甲醛的挾裹之中,衣櫃和書桌是薄脆的劣質品,電費本該是五毛一度,對……對……法律上這麼寫著,他翻倍翻到一塊二,我每個月要在用電方面支出正常尺度的兩倍多,還有五級能效的空調,如今的熱浪能把人活活烤出油,我能不用嗎?我已經想像出來了,他那傲慢的身軀拔地而起,俯視著貧窮的低產者,說我就把它們撂這兒了,你們怎麼樣!”
他換了個音色,換了個坐姿,換了副冷靜的神態去回應自己的話:“還有網路,我不提醒你的話,你恐怕就忘了!
“網路嘛,不知為什麼,網路時常斷開,房東不作為,我也無可奈何,我沒錢搬家,再搬,也是這樣的境地。此外,晚上是用網高峰期,出於一些我說不出的原理,網速會變成原來的十分之一,每次我看到斷網提示或者加載緩慢,我的拳頭就會驟然握緊,想要捏爆什麼,想要戳爛什麼,譬如別人的臉之類的,我且直說了吧,就是房東。我知道有解決辦法,像我先前說的搬家,或者認真起來,費時費力去研究寬頻,可是它們全加起來都不如戳爛房東的臉來得快樂,楊昕鵬,這是他的名字,租房協議上的身份證號赫然矚目,他才二十一歲,比我晚生一年,這樣逼仄的年紀,別人還被困在天真爛漫的學生時光裏,他就已經賺錢賺到手軟了,操他媽的,這樣的事超出我的認知,我需要原理。我對原理越是渴求,真相就離我越遠,像駁回降低租金的請求一樣,他輕鬆駁回了我所有控訴,不,不是你想的那樣,控訴只是個比喻,我是說,他極為怠慢地否定了我說的一切,他甚至不屑於親自動身過來同我爭吵,只是叫個保潔員過來看了看,得出結論說押金不能全退給你,得扣個四百五的清潔費,可合同上的清潔費只有七十五,除此之外,那麼窗臺呢?那麼樓板呢?還有該死的網路和電費呢?所有,囊括我深思熟慮的所有,對他來說簡直是棉花做的刀片,我打電話給物價局,稅務局,消費者協會,對他來說就像小孩子過家家一樣,嗯,好,我們知道了,我們會處理的,他們說的處理就是跟惡人沆瀣一氣,我講得沒錯吧?”
“正如你說的那樣,操楊昕鵬的血媽,但在此之前,你得有個鮮明顯眼的立場,你苦苦習得的大多觀點都得被推翻,而那從火焰中徐徐升起的、經過錘煉的閃著光芒的東西,才是你自內心凝聚的原生的珍寶。”
“我早知道法律是垃圾,我沒抱什麼期望,我只是對我自己的能力感到悲哀。”
“你以為自己學有所成。”
“對,我以為自己學有所成,好吧,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我從小到大經歷太多了,不去想也罷,但他是個什麼模樣的人已然很清楚,目前該有的疑慮是,他身處一個什麼模樣的系統裏,讓租客在私人開發的應用程式上交電費意味著瞞著法律幹齷齪事的遠不止他,只要欠費一分錢,屋裏的燈便啪地一下滅了,因為不像國家電網有寬限餘地,私心是沒有容忍度的,貧窮的低產者們被人用鐵柵欄圈起來,公司負責在他們上班的時候壓榨,管理鐵柵欄的人負責在他們下班回家後壓榨。我沒有錢,因為黑暗社會現存的各種費用把我剝了層皮,但我滿腹正義,我在扮演人們最唾棄的那種角色,楊昕鵬要扣掉我一半押金,經過我的操勞,我的奔波,我依然守不住那四百五十塊,我舉報他逃稅,舉報消防問題,還有許多無關緊要的事,我還是守不住那四百五十塊,反倒是他得意洋洋地對我說,你先前遲交房租,我倒沒追究哩,按理要罰上千塊,白紙黑字寫著!不錯,我住進來之前稀裏糊塗地簽了霸王合同,如今不僅誣責我牆壁生黴——這樣陰濕、終年不見陽光的環境裏,怎可能不生黴——還搬出合同上的混蛋條例,把我押金誆盡之餘,還想再訛上一筆,可他不曾想我在人權領域有最終解釋權,因為我就是判決者,我就是法律本身,他能想到嗎?他撓破頭都計算不來!”
“你是法律本身,而他是王八蛋。”
“他是王八蛋,他是忙碌的王八蛋,叫他派人來修個什麼,他總是淩晨才回復,我到底知曉了,他每天能收幾萬塊租金,遊走於中產者之間而無閒暇,他的城府比地府還深,可在我這兒,他的人情世故不頂用,吃透人情世故的人是最該死的。”
“你明天就要搬家了,你的抵抗在他耳裏只是徒然一聲犬吠,據說這些靠地產掙錢的人都手眼通天,你看,兇殺案幾天便沒了消息,跑空的房間很快又會被租滿,凶宅與否是他們說了算,要是有人得罪,就算逃去天涯海角,他們也能夠找到地址,你當真準備打這場仗?”
他沒有回答,拿起紙和筆就是回答。即使是撲一場空,他也要再寫一次檢舉信,檢舉些此前沒想到的,從自信到絕望是每個有抱負的法學生的必經路程,不必糾纏在無窮的懊悔裏,律師工作的精髓就是解開彎彎繞繞的條規,再精准地串聯起來,組成最有力的武器,他需要做的只是絞盡腦汁去想,把法典翻卷了頁腳,流逝掉整個夜晚,將近三十張黑壓壓的筆記紙摞起來,他的手指暈染著晶瑩的淤血,正以為得到了滿意的成果,他忽然不認識上面的字了,不知怎的,密集的漢字中,但凡有拉到底的豎筆劃,近末端的位置都會向右隆起一個圓弧——既熟悉又陌生的形狀,他無意識地繪出了如聖殤般的恐怖且未知的篇章。那些字勾掛著順時針轉九十度的“Ω”,像藤蔓結出來的果實,他察覺到自己必定在某個地方見過它們,他的思緒往那塊地方鑽,努力地回憶著,最後砰地一聲,有東西被鑽裂了,他開始無休止地生氣,無休止地表演刻板行為,他癲狂地跳起來,把昨晚撰寫的稿子撕成碎片,伏在牆上,抑或是有引力將他吸附在牆上,他瞪著突兀的眼珠子,無休止地書寫那個符號。淌成細絲的唾液掛在他的嘴角,他喃喃言語,我是法律本身,法律本身如是說,法律本身這樣規定:世界上所有寸土寸金的地方都該被炸掉,紐約,上海,香港。法律本身沒有義務陪這些無聊的人類玩下去,幾平米土地就是窮人的一生,被迫掰折自己骨頭,彎曲,蜷縮,盡可能壓緊自己,以便擠進比捕鼠籠還窄小的空心混凝土方塊裏,這些可憐蟲們,從窗戶伸出手就能摸到對面的窗,陰暗的巷子被遮罩,透不下一點光,這些可憐蟲們,任憑自己的養分遭人攫取,卻畢生查不明攫取他們的人是誰。把筆寫到沒墨之後,他生病了,他的喉嚨遭受炙烤,他的耳壓全然失衡,興許這是亂吃藥的結果,興許真正的催命鬼來了,也是拖耳壓失衡的福,他免去了人世的雜音,如今是盛夏,他只敢躲在冷氣裏覬覦窗外。意識惶惶如雲霧般撩動,鼻腔從此再也通不了氣,吸進的是象徵著不美好的東西,炙烤仍在持續著,如今最好的打算是,讓一切結束在無聊的炙烤之中,給生命留下一絲勉強能聽的尾聲。是的,真正的催命鬼來了,他甚至沒有上廁所的力量,打開窗戶盡是蟬鳴,關上窗戶又捉不住時間,沒有兩全的辦法,因為死期將至,遺詔的事宜必須提上日程。遺詔,他這麼稱呼自己未完成的幻夢,同時炙烤仍在繼續。藥片如山崩的滾石一樣瀉進他的嘴,平均吸一次鼻涕就會帶上兩聲咳嗽,事實就擺在這裏,他早知道這不是普通的感冒,發燒和一系列惡疾會接踵而至,當下的身體是屍體的替代符,既然懇求虛無沒用,不如痛斥虛無爽快些,值得注意的是,這不是什麼高大上的東西。他看著街道上匆匆來往的人,他們是早高峰的鬼,他們是新社會的鬼。
“末日來了,末日來了,我被混沌的重症侵害,食不了一丁點人間味道,我的鼻腔燃燒著,我的靈魂消亡著。”
他把自己的臉哭成好幾瓣,像花朵一樣盛開。
“我沒鬥過他,我沒鬥過。”
萬千瑣事自然收場,天亮了,他的鼻子堵得緊實,倘若揍上兩拳讓它開條縫,粘膜又會被空氣刺痛,空鼻症的苦楚無非如此,他帶著鼻音咒罵任何不順眼的東西,窒息感令他頭腦發昏,他抓撓自己的臉,企圖揭示病症的本來面目——細菌還是病毒的傑作?如果說是頑劣基因致使的,他並不情願接受這個答案,他抱著自己滿地打滾,掙扎,像條招笑的彈塗魚。
“我沒有鬥過他,我是法律本身,但我沒有鬥過他。混亂的人文和經濟架構支撐起現有的低維度法律,你知道這事很複雜,不可能有公平一說,各個產業相互鉤連,地產,可再生資源,食品和藥品,還有幼稚的股市,不論怎麼追溯,把負責印鈔和負責標價的全殺了,哪個國家的匯率高就炸掉哪個國家的金融機構,儘管嘲笑吧,總之我是高維度法律,在我看來,通貨膨脹是兒童的把戲。”他的病症仿佛得到了緩解,愜意地歎上幾大口氣,“以及最亟待解決的一點……我先前說過,諳悉人情世故的人是最該死的,可我有什麼辦法呢?不管位高權重的人還是普通人,他們的身體都是皮包肉,往心臟一刺都是死,這沒錯,可我也是皮包肉,我哪來的蠻力和巧技去幹偉大事業呢?”
因為這樣想,他又再度沉淪下來,針對自己的話,較好的法子是往鼻子裏灌芥末醬,較壞的法子是用衝擊鑽搗爛它,針對楊昕鵬的話,一時半會兒定不了刑罰,得閉上眼仔細想想才行,可他不能閉眼,他必須憑藉狂躁的心態活著,否則一靜下來,眼前所見的文字都會轉換成那個符號,譬如日曆上的數字“4”,他的大腦會想像最後一筆豎下來後繼續延長,然後畫一個偏右的鼓包,再一畫到底,任何存在下端未封截的豎筆劃的文字,都會被強制執行這樣的流程,好似被烙印在大腦上的咒語,接著更多魔咒得到印證,光是直線上凸起的圓弧已不足以撫平他的情緒,他還得想像那條弧線往中心遞增無數條弧線,到後來其他沒有豎筆劃的漢字也無法倖免,譬如“發現”的“現”,他會控制不住去想最後一筆豎彎鉤的凹陷部分像訂書針似地往裏排列,以形成密集的單點透視圖案,最後以右、左、下、右的順序打上一個倒三角,為了轉移注意力,他又瞥向房間門,可門框的一角也被他的想像力提取出來,單獨作為一個直角顯示,再如法炮製往裏複製遞增。失控的機械收束令原本崩潰的他瘋上加瘋,他拒絕相信人會突然患上以前從未出現的強迫症,也拒絕相信有什麼不可名狀的玩意在對他施加暗示,儘管後者的可信度似乎更高。他打開電腦嘗試搜索原因,流覽器頁面顯示網路未連接,這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這棟畜生公寓每天會斷至少二十次網,人們引導或被引導把責任歸到自己身上,他們被楊昕鵬的說辭安撫得服服帖帖,不少人莫名其妙砸了自己的路由器,卻從沒有想過拿張板凳捅爛走廊上的弱電箱,也沒人站出來,公佈所有人一直等待的解答。等網路恢復了,他點下刷新按鈕,加載圖示車軲轆似地轉圈,時間久到他開始懷疑的那一刻,預感來了。
“狗網!操你媽,狗網!狗網!再斷一次,只要再斷一次,我就開始行動,雖然不知道你是誰,但他的生死由你決定。”他切著齒說,猙獰地搖頭晃腦,要裂眥一般。
網路連接失敗。
他卸下了枷鎖,多年來他為尋找鑰匙東奔西走,沒曾想會被稀裏糊塗地解開,原本絞他心的刑具揪擰到極致,再也運轉不動了。他一生氣就會流出清水鼻涕,堵塞的鼻子沒法吸它們回去,他頂著亮閃閃的人中在地上爬行,尖叫,打挺,翻箱倒櫃,抽屜裏留有一把老式闊剪,也許是上個租客留下的,不偏不倚掉在他身邊,若是正紮進他的胸口,意思是讓他儘快死了好,但它躺在他的手邊,那麼教諭便一目了然,包括他卑劣的鼻炎,原先只是噴點藥就通了,後來感冒讓鼻炎惡化,外耳道發炎是順帶的禮物,怎麼弄也無濟於事,這也是教諭的一部分。因為受到窒息感的支配,他攜著悲茫和錯愕,以及簌簌涕聲,似落水者一樣大口吸氣,濃稠的粘液卡在鼻翼位置,吸幾口氣又嗆出來,他拿著剪刀走出門,以這樣的外征出現在人們眼前,也正是遭到他們詫異目光的脅迫,他感到自己被公有化,原本就愛把人往死裏盯的中老年人滯愣住了,注視著這個不事先告知便在公共場合冒失登場的丑角,他們光是注視而不思考,腦子裏裝著幾十年人生的迴響。
“咳咳……咳咳……”他困乏地啟用嗓子,低沉的病音斷斷續續,其間又在不明地應答,“嗯……嗯……咳咳……好……”
他一概知道楊昕鵬在哪,他知道楊昕鵬為當房東專開了一間掛滿鑰匙的辦公室,擁有四五棟樓,幾千個租戶,故而每一個租戶都被當作幾千分之一的人看待,當人瓦解成幾千分之一,那就和蟲子沒什麼區別,誰又會把蟲子當回事,然而除辦公室外,楊昕鵬真正的穴居處必然是接近市中心的某個殘舊卻昂貴的老小區,至此又不得不用此前鑒定頑劣事物的方法來鑒定它,任何與物理價值相斥的溢價都該被消滅,去逮著人類問為什麼,他們只會甕聲甕氣地說,地段如此……地段如此……價格浮動孕育罪惡,一個公理可以闡明一切,只需要一個就好,破開枷鎖的下個目標就是找到那個公理,闡明就足夠了,解決辦法要靠噴薄的鮮血去發現。講到楊昕鵬,他們是這樣一群人,早在很久之前,也許自出生那天,被人從陰道裏拔出來那天就被規則管教好了,社會沒錯,出什麼岔子都是自己的問題,其實不是的,假如中國社會是個具體的生物,那它就該被推上刑場去砍頭,他們不會往這想,同樣是這群被訓得整整齊齊的人,隨著年齡增長而漸漸狡詐起來,他們適應規則並與之融為一體,把為人處世設計成一套演算法,利用狗操的規則去害人。
他是法律本身,他也有一套不賴的演算法,眼下坐在對面公寓樓辦公室的楊昕鵬是被演算法抽出來的樣品,所以他無需害怕,反而應當興奮才對,把聊以自慰的話想盡後,他才擠出一丁點笑容,坦蕩地走上樓梯,熱力緊緊裹著他,一條條汗線從上至下劃過脊背。二樓是麻將館,充斥著獐頭鼠目的裸露著啤酒肚的老男人,他們有些是替楊昕鵬管理公寓的人,再上面才是他的終點,許久以前被租房仲介稀裏糊塗拉來簽合同的地方,當時滿屋的楠木氣味,如今再也聞不見了,他推開門,冷氣給他帶來舒心的涼爽。楊昕鵬正伏案寫些什麼,抬頭問他要幹嘛,他只是用上畢生力量吸一口氣,狠狠教訓一番充血的鼻腔粘膜,然後被掉進喉嚨的鼻涕惹得大聲咳嗽。
來做什麼?楊昕鵬再次問道,他的視線被電腦顯示器擋住,沒有看見剪刀。
“我今天搬家。”
哪個?
“今天搬家的那個。”
找不到,手機上給我彈個消息。
“你不認識我?”
楊昕鵬放下手裏的筆,歪著頭,頗為考究地打量他,隨後試探性地,以確認對方精神狀況為目的又說了一次:手機上彈消息。
“我是被你鋸掉窗臺的人,我是被你克扣押金的人。”
楊昕鵬隱約嘖了聲,點點頭,無言以應答,他如此年輕,如此纖瘦,兩顆荔枝大的眼球體現出獨屬於二十歲青年的俊俏,像被整塊塞進去的顴骨又使他看起來極其老沉。
“我記不清什麼時候的事,讓我帶著呼吸器官出生,卻又不讓我呼吸,我失去了一個生物體本該擁有的最基礎的生理行為,這是致死的殘疾,鼻粘膜的熱辣使我徹夜難眠,困倦令我頭昏腦脹,我分不清病情在惡化還是在痊癒……真是可笑,祈求著把鼻涕全弄出來就萬事大吉,其實沒這回事,該死的人到頭難逃一死,我擅長自我蒙蔽,假想耳壓沒有問題來麻痹自己,睡一晚明天就好了,沒好的話再睡一晚,要是明明快好了還去看醫生,錢就白花了,生活也沒著落了,不然能怎樣呢?我甚至沒錢搬家,我生來被分配的任務就是隱忍痛苦,我沒日沒夜哼唧著,像個骨頭要散架的老頭,顫顫巍巍例行生活瑣事,還止不住考慮到底先有痛覺還是現有痛苦這種無聊的哲學問題,不然能怎樣呢?你看,因為說話沒有鼻音,我就這樣莫名變成了山西人,我被世界的無常東拉西扯,被拽成四五塊,我今天拼回來了,就這樣站在你面前,先前我出門那一刹那還覺得不可思議,我就這樣在裏面度過了整個夏天嗎,還是說往後周而復始地痛苦?退房保潔費七十五塊,為什麼清清楚楚寫在合同上的能被一句話判定無效,每當我自覺即將抵達正義的時候,都會有一道看不見的牆攔著我,我氣急敗壞地用腦袋撞牆,只看見一灘血豎直懸在我眼前,也就是說,我用了獻祭生命的方法,到頭來也只能盯著自己的血。”
自言自語能解決什麼嗎?我不想再解釋了,我在電話裏跟你解釋過不下十遍。灶台上都是油漬,牆壁上都是黴菌,一切很明瞭,你今天搬走,我們就再無糾葛,你還來耍潑做什麼?
“我不是來解決什麼的,你們總覺得動身就必須結算一項事務,單單是詰問的話,你們會斷定這是不成熟的表現,我原以為我會變成靠詰問謀生的人,我身邊的人都這麼覺得,最開始來到這個城市的時候,我天真地覺得只要注視苦難就行了,沒曾想惡鬼群棲,連空氣都在毒殺我,那天我被仲介帶過來,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仲介,也不知道掏出這個城市平均工資的四分之一拿來租房,也只能租到和地下室沒差的陰濕牢籠,這還不是最可怕的,對面那間牢籠哪怕沒有窗戶也開價八百,真是好大的胃口,他詐走我仲介費,你詐走我不盡的壽命,你們藏匿在惡之城裏,揩掉每個過路人的血肉,我也是其中之一。現在我拖著露骨的殘軀來到你眼前,就是在等你露出滿意的笑容,說實話,你是一個很穩健的人,所以我很想看你發自內心地笑一次,而不是佯裝禮貌的微笑,這樣,你且先笑個過癮,我很快會對你做出判決,他也一樣。”
我過去幾年裏見過上百個像你一樣裝可憐的人,他們沒有從我這裏成功拿到一分錢,一分都沒有。判決?你是來判決什麼呢?博不到同情心就開始裝作自己是個厲害人物,是嗎?
“是的。”
我希望你知道,你已經浪費我太多時間了。
“我知道的比你想的要多,如果我選擇答應這個世界,去麻木,去從惡,去學習作奸犯科,我很快就能入門,順便拿個技能證書什麼的,但我把脖子伸得很長很長,雖然被你們踩著,其實我已經高過你們了——關於某種越過天際的邪惡,我看得到他們,他們監控人民在網上說的話,他們扣押人民在銀行存的錢,還有什麼?還有,在自己開的店裏午休要罰款,電動車有後座卻禁止載人,再往外看,還有規定女人必須戴頭巾的國家,但凡人們一天不群聚起來端掉這種垃圾法律,那全人類都是敗類,因為太過清醒,我看到的世界解析度高得嚇人,再不對它提起訴訟就沒時間了,說到頭,我就是法律。”
你說你是什麼?那好……那好……楊昕鵬起身走到一旁的檔櫃前,慢吞吞翻找著,你叫什麼?是今天到期嗎?我看看……是莊曜廷嗎?那就是你了,我們把合同放桌上,打開天窗說亮話,你不服氣,我一個字一個字掰開跟你講清楚……當他拿著檔袋轉身時,剪刀嵌入他的胸口,刺破他的心臟,莊曜廷離他很近,只有三十多公分,右手軟綿綿地搭在剪刀把上,看起來完全沒有要取人性命的兇狠模樣,只是耷拉著肩站在這個敞亮的房間裏,吸溜著鼻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失落。莊曜廷拔出剪刀的時候,他的白色襯衫飛速染上這輩子都洗不乾淨的血跡,他大喊一聲,既像呼救又像自瀆,更可能是某個人名,他撲倒在沙發椅上,大聲喘著粗氣,莊曜廷掀開他的襯衫,從肚臍位置向上剪,把他的腸子挑出來一根根剪斷,得益於提前被命運堵住鼻子,才能無視糞液的腥臭,才能時不時抹下積目的眼穢,像個做針線活的老太太,平極了氣息坐這兒,沐浴暫時免費的陽光。
他袒露著碎麵條似的腸子,安詳地平躺在地上。
莊曜廷走下樓時,打麻將的人依舊在打麻將,他們總是說話說得好好的,嗓音忽地拉得比天要高,隨後又恢復平靜,如同教書先生似的,把大道理向在座的賭徒徐徐道來。莊曜廷脫下深紅色的髒衣服,扔到樓道上的垃圾桶裏,享受無盡的釋然,然而唯一害怕的是,多年後的某一天,耳壓突然恢復,外界明朗起來,不下心聽見真實的一面,那時候已經不存在所謂的自救的辯法了,因為洪流也好,駭浪也好,救活就是死掉,死掉就是救活。
1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HVIZfAyiP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