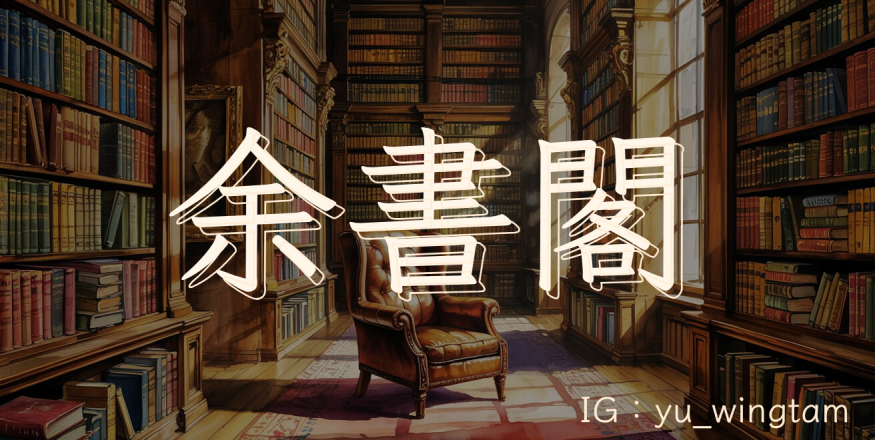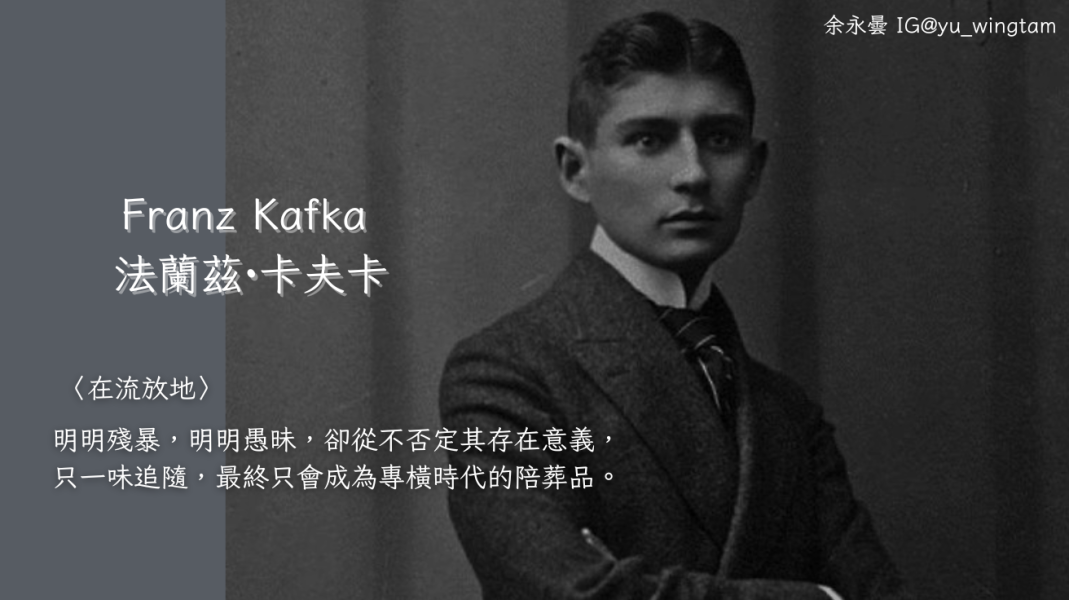
卡夫卡〈在流放地〉
內容概要
一個周遊列國的旅行家,來到一個被用作為流放地的小鎮,因受到司令官的邀請而觀賞一場殘酷的行刑。
受刑人是一個小兵,有人報告他不去站崗,跑去偷懶睡覺,被發現捉到後,還抱着上級褲管,說話囂張跋扈。
但對負責行刑的軍官來說,受刑人犯什麼錯,事情的原由是怎樣,這些都毫不重要。軍官想向旅行家介紹的,只有那件由前任司令官發明的精密刑具,以及其奇異的行刑過程。
刑具分為三部份,最底層是床,受刑人將臥在其上,然後會有一個插滿鋼針的耙子降下來,扎在受刑人的後背。耙子上方懸掛着一個和床一樣大小的箱子,名「設計師」,裡面全是齒輪,只要通過調教齒輪,耙子上的針便會在受刑人背上刻字,刻足十二小時,直到受刑人失血過多而死。
本來軍官想通過向旅行家展示這個設計精密的刑具,博得他對這種制度的支持,從而阻止新司令官廢除這一制度的決定。
但生活在自由國家的旅行家,卻覺得這樣的做法殘暴而不人道。得知旅行家與自己意見不一,軍官也沒有強求,在無法挽留這個制度的情況下,他最後決定要這個制度一起滅亡。
他躺上刑具的棉花床,啟動機器,鋼針沒有如他料想中將他慢慢折磨至死,而是一下子穿過他的身軀。
看完這場如鬧劇的行刑後,旅行家匆匆離開了流放地。
99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X2EF9PticM
讀後感
權力象徵
在閱讀論文時,發現有不少學者都提出,在流放地的行刑不是為了公義,而只是一場權力的顯擺。
所謂「犯人」,沒有為自己辯護的機會,甚至連自己犯什麼罪、受什麼刑都不清楚的情況下,迎來殘酷的死亡。
其實有沒有犯罪,公義有沒有得到伸張,根本就無人在意。
可能只是某位軍官需要出出氣,負責處刑的法官想再舉辦一次瀰漫血腥味的狂歡盛會,一個無辜而奴性的小人物就這樣剛好被找上,一場毫無意義而殘酷的死刑就此拉開序幕。
書中軍官渴望暴力,而暴力背後是對權力的掌控。
在這個故事裡,殺一個人,不是因為那人犯了多大的錯;只是殺人的人,想顯擺自己擁有隨意捨棄他人生命的權力。掌握權力的一方,便同時掌握所謂「正義」和「公理」。
這就是專權的本質,一個只有掌權者與人命如草芥的世界。
99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eOiBm2ws9M
人異化而來的機器齒輪
自18世紀工業革命,科技成為帶領人類進步、發展文明的重要工具。直到一戰爆發,人類第一次感受到科技的反噬。
機械既能服務人類,亦能毁滅人類。
若把機械放進政治語境來看,有學者認為,卡夫卡的殺人機器其實是在影射當時專制殘暴的奧匈政權。
國家機器的運作,自然離不開一眾人民。
在專制制度下,人民是沒有知情權,他們只不過是整個國家機器一個微小的齒輪,日復一日重複同樣的工作,不必知道這樣做的意義,也不必了解其他人的工作,只是一味勞動,直到自己大腦裡的齒輪因長時間沒有使用而生鏽荒廢,喪失思考能力,身體仍然枯燥地重複同樣的工作。
如此麻木的勞動,經過長時間的重複,人類會把它視為理所當然的工作,甚至發展成狂熱的信仰。
小說中的軍官,總是在回憶過去司令官在這片流放地用他所設計的刑具處決犯人的「威風」畫面。那時,往往有一大群人來湊熱鬧,座無虛席,沒有人質疑刑罰的兇殘,他們都是這種刑罰的追隨者。
就算昔日的司令官去世,新人上任,這不人道的刑罰將被永久廢除,作為刑法的忠心追隨者的軍官,仍然執着於這樣兇殘的殺戮機器,視之為自己的人生意義,甘心成為一部機器的奴僕。
直到最後,旅行者否定機器的存在,這項刑罰的滅亡結局已成定局,已被異化成機器齒輪的軍官選擇與這部與他人生意義綁定在一起的機器一同滅亡。
明明殘暴,明明愚昧,卻從不否定其存在意義,只一味追隨,最終只會成為專橫時代的陪葬品。反抗無門,自然是可悲的。但連反抗也不反抗,甚至沒有意識到這是一種壓迫,反被各種宣傳洗腦,將其美化成某種美德或精神,這才是最可悲的。
99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4k05r5Yu68
評分
喜歡程度:6/10
易讀性:6/10
上述內容若有錯漏,還請各位不吝賜教。
如果喜歡我的內容,請點讚,感興趣的話可以追蹤一下帳號,每逢週日更新書評,感謝你們支持。
99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8Nwi991yjE
參考書目
孫彩霞:〈刑罰的意味——卡夫卡《在流放地》與余華《一九八六年》的比較研究〉,《當代文壇》,2003年03期,頁49-51。
曾艷兵、屠琳盈:〈儀式與暴力——論卡夫卡《在流放地》〉,《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19年01期,頁55-63。
路楊:〈流放地上的權力狂歡——論卡夫卡《在流放地》的主題〉,《名作欣賞》,2009年18期,頁9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