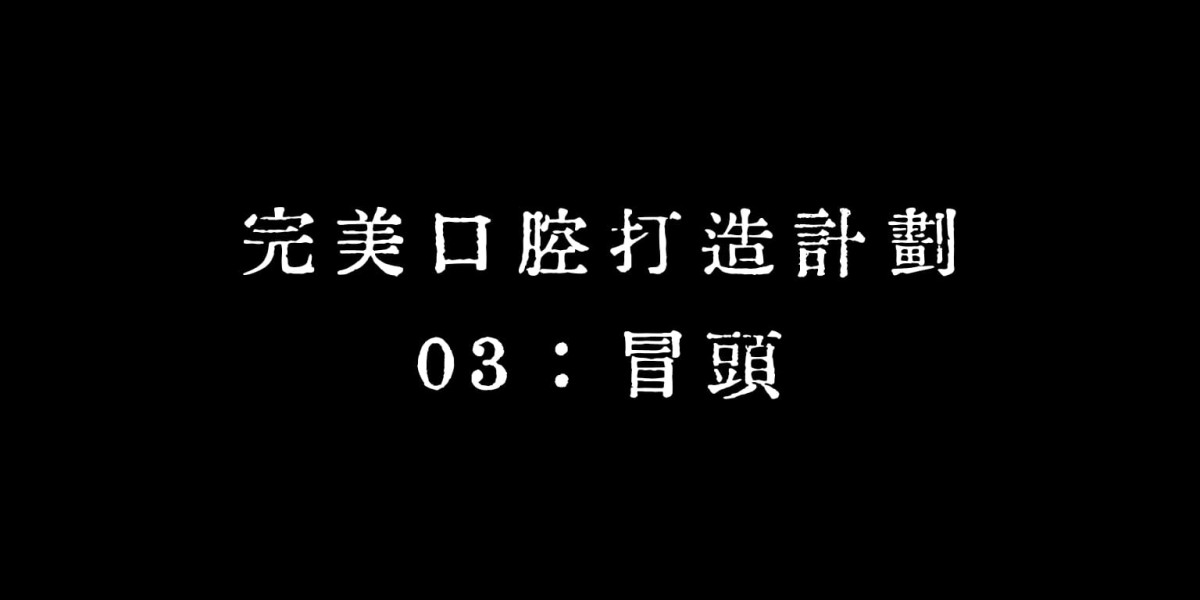 x
x
為儘快把凶徒緝拿歸案,警方延長了受害人遺體在殮房的存放時限,用以刑事調查用途,怎奈查無實證,只好通知死者家屬辦理認領手續。緊接着是委託合適的殮葬商,籌備維新喪禮,篩選不富貴不寒酸的環保棺,向遠房親戚及公司同事發送請柬,諸多事宜,直至喪禮當天已經三個月過去了。
往好的方向想,很感謝獵牙人,令龔亮熒有個停薪留職的長假期。
靈堂祭壇盡是粉紅色滿天星,宛若花圃,乃龔若曦生前最愛的花,寓意甜美青春。遺照則是私拍寫真的兔女郎裝扮,仰面看鏡頭,跪着撩頭髮,活脫就是向褲襠討吃胡蘿蔔,性感尤物,怕是她想要被記住的方式吧。靈桌擺放的供品亦非齋菜及生果,而是草莓檸檬派和栗子奶油派等甜點,待會親友們也可分來吃,正如昔日她時常貪心點了滿桌菜,偏又怕胖沒能吃完,便打包回公司慰勞大家。
龔亮熒坐在靈堂左邊的主家席,穿着白色寬版上衣與杏色繭型寬褲,省去披麻戴孝的傳統,挺腰、翹腳、兩手交疊放在膝蓋上,原是率性悠閑的服裝,卻因她的舉止拘謹而顯得沉穩。
斜眼瞄向靈堂入口,看着親友在接待處留下簽名,致送帛金,雖則不是可疑人物,但循例被兩名彪形大漢攔住,稍作搜身才可通過。皆因近年愈來愈多變態偷闖猥褻屍體,即使殮葬商把提供保鑣包括在套餐內,仍難起到阻嚇作用,基於支配慾或挫敗感都囤積到姦屍發洩的境地,誰管你肌肉有多壯?相比這些道德淪喪,龔亮熒更在意為何三姑六婆二舅四叔全到齊了,依然僅見零星幾位同事?
這時菜鳥阿魏照着堂倌指示,行三鞠躬、家屬謝禮、點亮香薰蠟燭代替上香。
「熒姐,超級久沒看到你,有好點嗎?」阿魏走到主家席前,俯身慰問。
「別擔心我。」龔亮熒舉目四望,很少正眼看人:「馨姐在哪,女同事集體失蹤?」
「馨姐和她們辭職不幹了,整個部門陽盛陰衰⋯⋯」阿魏憨憨地搔搔頭,不敢大聲張揚,免得衰事連發打擾到其他悼念者,即忙坐到旁邊的空座位,靠近耳語:「那個獵牙人專挑女主播下手,到現在還沒逮到他,三個月內三宗謀殺,尤其女性,當記者是目前最高危的職業⋯⋯」
龔亮熒聞言扭過頭來,斂首低眉,似乎盤算着甚麼,反過來輕拍對方後背示意。
「這可能是好事,何苦搭上性命當一面照妖鏡?」
隨着來賓陸續向逝者致哀,告別式臨近結束,龔亮熒站在靈堂門口派發吉儀,送行排隊離場的親友。跟在隊尾的是總監盧興邦,方才靜默禮成就坐到老遠的他,惆悵地接過吉儀,那前額禿髮變得如橘子發霉般灰白,看來這波保命離職潮,給他徒增了不少煩惱。
「老公在家看孩子吧,應付得來嗎?」總監注意到下屬腹部變平,借意打開話題。
「對,我半夜餵奶也太崩潰了,該輪到他照顧。」龔亮熒隻字不提失胎失婚,無謂換來假裝關心,顧左右而言他:「你呢?頭髮白得那麼焦急,在愁甚麼?」
盧興邦不自在地搓手,難於在兩名保鑣側近傾談私事,提議出去外面聊。
兩人來到離殯儀館不遠的狹長小巷,數幢鄰接的屏風樓將天空收窄,紙皮箱及發泡膠堆滿路邊,排風口冒起油煙,熏黑滿是裂縫的混凝土牆,但仍能看到「全民領取綜援金,返工留給機器人」等塗鴉字句。然而盧興邦好像在嫌空氣不夠污濁,急着從口袋掏出菸盒,拔出菸叼在嘴裏,點着了便是大口猛抽,堪比燃煤發電廠的廢氣排放量,到底是有多大壓力才抽得如此兇狠?
「我老媽是廿年老菸槍,都沒有你誇張,你甚麼時候開始抽的?」
「最近兩個月,」他閉目抬頭,感受尼古丁滲透血液,「世界愈來愈黑暗了。」
「這個世界黑暗很久了,你是傻西瓜嗎?」龔亮熒無奈得皺眉,蔑笑道。
「不至於像是奪命狂兇和智能叛變同時上映吧?我以前認為這叫務實,不用跟着紅線走,別踩在上面就行,可是我逐漸覺得自己只是個犬儒主義者,否定絕對的道德真理,滿足那種眾醉獨醒的感覺。如果當初我能聽從內心,而不是自以為很理性的腦袋,這個地方會變怎樣?」
「別看得自己太重要,把毫無關聯的事情混為一談,以為做得更多,做得更好,就能避開那些盲目而無序的劫數,無非自我欺騙。勤勞耕作的會旱災失收,道德高尚的要死刑伺候,這個才是現實。」
「照你這樣說,難道那個獵牙人配有好結果?」盧興邦糾結得搖了搖頭。
「如果聽完能讓你好過點,我保證他有個超地獄的童年。」龔亮熒輕忽帶過,從褲袋拿出扁圓形鈦酒壺,扭開蓋子,往嘴裏大灌兩口,寄託於防止自殺的成癮物,打趣道:「你抽菸提神,我喝酒賣醉,是不是很有眾醉獨醒的感覺?」
「這都被你挖苦,真是多難興邦。」總監抿着嘴笑,特別喜歡下屬奇怪的幽默感。
所謂無事不登三寶殿,龔亮熒大抵能猜到上司的來意,並非單純想要聊心事,分享絕望,博取共鳴,既然遠談不上有真知灼見,那就改為聊公事。自知不合時宜又不近人情的盧興邦,難為情得搔着後頸,手指還夾着菸,無暇顧及會否燒着所剩無幾的頭髮,實在走投無路了,才厚着臉皮提出請求。
「對了,雖然女記者被看作高危職業,但公司嚴重缺人,你能不能提前復職?」
「誒⋯⋯」龔亮熒裝作猶豫,以掩飾真正意圖。
「抑或你要辭請當全職主婦也行,別勉強,我不會放在心上!」
「復職不是問題,前提是我得聘請外傭打點家務,大家熟歸熟,總不能為了個人原因要求加薪吧,該有的專業還是要有,除非我有額外貢獻,否則只是趁機佔便宜。」龔亮熒板起臉,向前挪了幾步,走到盧總監對面的那堵牆下,倒轉酒壺,手舉過頭,盯視着深紅如血的葡萄酒澆進臭水溝,「你能讓我擔任新聞主播,我也會兼顧撰稿,確保我所說的話是來自我的想法,僅限兇殺案和姦屍案,別的報導我會照着提詞機念,你能接受這點嗎?」
眼看盧興邦如釋重負地耷拉着腦袋,連着菸霧長舒了口氣,主播崗位無疑已收入囊中。他把菸頭掐熄在自備的不銹鋼菸灰盒裏,置身髒無可髒的巷弄,依然保持着無濟於事的公德心,他品性如此,以致慶幸愛徒回巢才不到半秒,便擔心起職員的人身安全,「你開出的條件很合理,不過為甚麼當所有女生都搶着離職,你卻往火場裏衝,由幕後走到幕前?」
他欲言又止,頓了片刻道:「你連死都不怕嗎?」
當時正巧踏入午市,後巷風口再次噴出大量烹飪油煙,在龔亮熒頭上奔湧而下,整個身影頓時陷入瘴氣之中。扁鼻薄唇瞬間被炙熱的白霧淹沒,剩得寬衣闊褲的輪廓線,於迷濛中攤開雙手,既似推卸責任又如迎接感召:「因公殉職,我就不用再交薪俸薪了。」
ns18.226.82.161da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