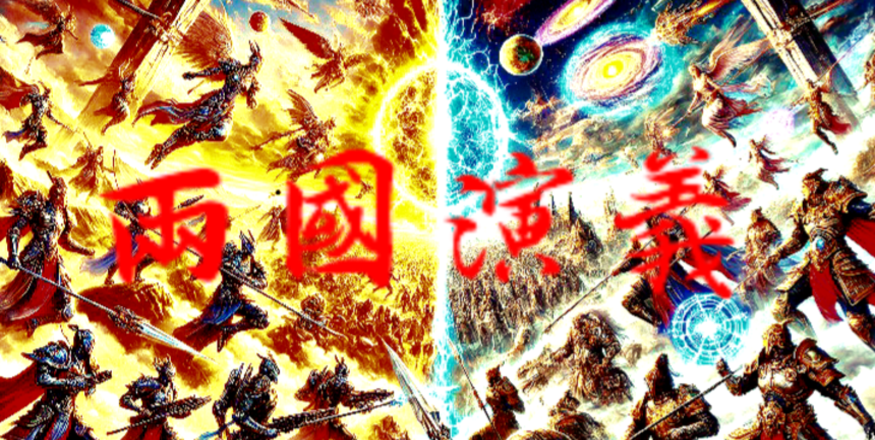血雨洗去戰場塵灰,鐵蹄踏碎萬骨焦屍。男軍的主力部隊,在江俊毅的號令下,帶著滿身創痕退入了提特城——這座堅固的要塞,成為他們短暫的避風港,也是下一場戰爭的前沿據點。
提特城外,戰敗的殘軍如潮水湧入。城門一一打開,守將早已等候在側,臉色鐵青迎接這支滿目瘡痍的大軍。
城內街道,盔甲破裂的士兵被抬進軍醫營,哭號與呻吟此起彼落。
江俊毅騎在沒有馬鞍的坐騎上,身披焦黑戰袍,鮮血染紅的肩甲依舊散發著餘溫。
他抬頭望向提特城的高牆,對身旁軍官低聲說:「杜那諾是我們的死敵。曾秉豐、陳茂雄,他們……必須葬在戰火之中。」
幾名高階將領在他身後列隊而立——陳韋勳滿臉蒼白,仍舊咬牙撐著;劉永浤右臂打著夾板,步履踉蹌;何勝勳滿身創痕,卻依舊一身鐵骨。他們都不發一語,只有行軍禮。
當晚,夜幕籠罩提特城,城外烽火仍在遠方閃爍,戰馬的喘鳴聲混雜著傷兵的低吟,讓空氣壓抑得幾乎令人窒息。
大殿之中,一盞巨燭搖曳,光影在粗糙的牆壁上晃動。
陳韋勳坐在長桌一端,身披淺金戰袍,胸口纏著厚厚的繃帶,臉色蒼白。他捏緊酒盞,指節泛白,聲音壓得極低:「你們……有誰能告訴我,曾秉豐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強?」
他抬起眼,目光掃過在座的幾位戰將。
何勝勳沉默片刻,粗壯的手臂擱在桌上,巨槌立於一旁。他眉心皺得緊緊的,搖頭道:「我記得他,從來不是這種人。他的身手……本就不弱,但絕不是今日那種……幾乎是神魔的境界。」
劉永浤坐在另一側,身穿簡化過的鋼甲,半邊臂甲拆開,露出還未痊癒的創口。他的聲音略帶金屬顫音:「我用能量探測時……感覺他的氣場完全超出了人類範疇,像是……某種強制提煉過的存在。可是……我找不到來源。」
陳韋勳咬牙,低聲咆哮:「我們幾個,聯手都擋不住他!江司令也……也被擊倒……」
桌邊陷入死寂。只有燭火在無聲地抖動,映照每個人臉上的陰影。
這時,厚重的銅門緩緩打開,一道紅影踏入。
江俊毅。
他仍披著那副殘破卻重新綁緊的紅甲,肩頭鎧片斷裂處綁了麻布條,神情卻冷若鋼鐵。他一步步走進燭光,聲音低沉卻帶著壓不住的殺意:「你們說得沒錯。」
他停下腳步,俯視桌邊的將領們,眼神如燃燒的餘火。
「曾秉豐……一定修習了某種神功。」
江俊毅的聲音壓得沉重,每個字像是鐵錘砸在眾將心口:「普通的武學,不可能讓一個人凌駕整個軍隊。這股力量……必然來自我們未知的禁忌。」
阿卡薩拉平原上的杜那諾城燈火通明。火盆在廣場四周燃燒,酒香、肉香、鮮血與煙火交織在一起,成為屬於勝者的夜色氣息。
杜那諾軍,贏了。他們擊退了男軍鐵騎,守住了叛旗,甚至將江俊毅、陳韋勳等名震大陸的將星,全部逼退——這場戰爭,足以寫進史詩!
廣場中央,數百名杜那諾士兵圍坐在火堆旁,大口飲酒,大聲高歌。牛腿在火上烤得油脂四溢,烈酒如溪流灌入粗獷的喉嚨,戰士們的歡呼聲直衝雲霄。
而最吸引目光的,莫過於那群影炎衛叛徒——全軍中最致命也最絕色的舞姬戰士。
她們換下戰甲,披上薄紗,足踝繫著金鈴,在烈火旁赤足起舞。長髮隨風飛舞,雪膚在火光映照下泛出暖金色,腰身如蛇般柔軟,每一個轉身都牽動士兵的驚呼。
「來,再近一點!」有人大喊,舉起酒杯。
一名影炎衛女子微笑,走過去,將一杯烈酒送到他的唇邊,指尖輕輕劃過他的頰側,讓他瞬間心跳失序。
另一名舞姬在鼓聲中旋轉,腰間的薄紗一拂,露出筆直的長腿,腳踝鈴鐺隨著她的每一步發出清脆聲響,挑逗得士兵們如狼般咆哮!
「今晚,我們屬於勝利!」一名將領高舉酒盞吼道,身邊的影炎衛立刻伏在他懷裡,低聲呢喃:「將軍,您才是今晚的王。」
酒意與戰意交織,整個杜那諾城像是燃燒的火盆,欲望與狂喜在烈焰中升騰。
而在高台之上,曾秉豐披著黑袍,靜靜坐在王座似的石椅上,目光俯瞰這場狂歡。燭火映照他的臉龐,那一抹笑意冷酷而自信。
「勝利,是最好的號角。」他低語,舉起酒杯,黑氣在酒液中翻騰,如同未散的殺意。
廣場火光沖天,火盆的烈焰將夜空映得通紅,酒香與烤肉的油脂香氣交織,混雜著戰士們的笑聲與歌聲,彷彿要將戰場的血腥與殞地洗淨。數百名杜那諾士兵圍坐在火堆旁,粗糙的酒盞高舉,烈酒如溪流般灌入喉嚨,濺得盔甲與地面一片狼藉。戰士們的吼聲震天,有人醉態可掬地摔倒在地,卻引來更大的哄笑。
影炎衛的舞姬們在火光中翩然起舞,薄紗如雲,隨她們的旋轉飄揚,露出雪白的腰肢與修長的雙腿。金鈴在足踝叮鈴作響,每一步都似踩在士兵們的心跳上。火光映照她們的臉龐,笑意嫵媚而致命,戰士們的目光追隨她們的身影,眼中燃燒著比火堆更熾熱的渴望。一名舞姬俯身,將酒盞遞到一名士兵唇邊,指尖輕撫他的下巴,引來一陣狼嚎般的歡呼。另一名舞姬在鼓聲中旋身,長髮甩出弧線,薄紗滑落肩頭,露出半邊香肩,士兵們的酒杯幾乎捏碎,吼聲響徹夜空。
「今晚無醉不歸!」一名杜那諾將領高舉酒盞,聲如洪鐘,身旁兩名影炎衛女子依偎而來,一人為他斟酒,一人輕聲低語,嬌笑聲讓他豪氣倍增,猛灌一口烈酒,酒液順著鬍鬚滴落,引來更多笑聲。廣場上,烤牛腿的油脂滴入火堆,火焰竄起,映照出戰士們滿是塵血的臉龐,卻掩不住勝利的狂喜。
高台之上,曾秉豐靜坐於石椅,黑色長袍在夜風中微微翻動,手中酒盞中黑氣繚繞,彷彿連酒液都帶著他的殺意。他的目光冷靜而深邃,俯瞰廣場上的狂歡,嘴角噙著一抹若有若無的笑意。魔刃「噬魂」斜靠在石椅旁,刀身隱隱嗡鳴,似在回味戰場的血腥盛宴。
一陣沉重的腳步聲從高台後方傳來,陳茂雄大步走來,身披暗灰戰袍,左手臂上的橘紅法印依然散發微光,宛如未熄的烈焰。他的步伐穩健,每一步都讓石板微微震顫,氣勢如山。他手中提著一壇烈酒,嘴角揚起一抹豪邁的笑意,目光鎖定曾秉豐。
「喂!」陳茂雄的聲音粗獷,帶著幾分挑釁,「你這傢伙,坐在這裝什麼冷酷?戰場上殺得痛快,現在不跟弟兄們喝幾杯,算什麼英雄?」
曾秉豐微微抬眼,黑瞳中閃過一絲興味,卻不動聲色。「喝酒?哼,這些凡夫俗子的狂歡,與我何干?」
陳茂雄哈哈大笑,猛地將酒壇擲向曾秉豐。曾秉豐隨手一接,酒壇穩穩落入掌中,酒液未濺分毫。他低頭看了一眼,嘴角扯出一道冷笑:「你這傢伙,倒是有幾分膽量。」
「少廢話!」陳茂雄大步上前,一屁股坐在石椅旁,隨手從腰間掏出另一壇烈酒,拍開封泥,濃烈的酒香瞬間瀰漫。他舉壇對曾秉豐一敬,豪邁道:「你我今日聯手,宰了男軍十萬鐵騎,這種勝仗,不喝個痛快,怎麼對得起這片血染的阿卡薩拉平原?」
曾秉豐目光微動,終於起身,緩緩走下高台,手中酒壇輕晃,黑氣在酒液中翻騰。他冷聲道:「好,既然你有這興致,我便陪你一場。」
廣場中央,士兵們見曾秉豐與陳茂雄並肩而來,頓時爆發出震天的歡呼。影炎衛的舞姬們停下舞步,目光流轉,落在這兩位戰場之神身上,眼中閃過敬畏與好奇。陳茂雄哈哈一笑,猛灌一口烈酒,隨手將酒壇扔向一名士兵,吼道:「都別愣著!今晚不醉不歸!」
士兵接住酒壇,激動得手顫,連聲喊道:「為陳將軍!為曾大人!乾!」他猛灌一口,酒液濺滿盔甲,引來一片哄笑。曾秉豐冷哼一聲,卻也舉起酒壇,緩緩傾倒,酒液如瀑,順著喉嚨灌下,黑氣在酒液中散開,宛如暗夜中的星火。他的動作冷靜而從容,卻讓周圍的士兵心生敬畏,連聲高呼:「曾大人!無敵!」
一名影炎衛女子款款走來,手中托著一盤烤得金黃的牛肉,笑意嫵媚,遞到陳茂雄面前:「將軍,嘗嘗這戰後的滋味?」陳茂雄大笑,接過牛肉,大口撕咬,油脂順著嘴角流下,他抹了一把,豪邁道:「好!這才叫痛快!」
另一名舞姬走近曾秉豐,足踝金鈴輕響,薄紗下的身姿若隱若現。她遞上一盞烈酒,低聲道:「大人,您的刀法如神,妾身敬您一杯。」曾秉豐目光掃過她,眼中無波,卻接過酒盞,一飲而盡。酒液入喉,黑氣自他嘴角溢出,舞姬嬌笑一聲,卻不敢再靠近。
陳茂雄拍了拍曾秉豐的肩頭,笑道:「你這傢伙,連喝酒都帶著殺氣!來,咱們比比誰先醉倒!」他猛灌一口,酒液濺得滿身,引來士兵們的歡呼。曾秉豐冷笑,酒壇一傾,烈酒如瀑,盡數入喉,黑氣繚繞,氣勢不減。
廣場上的火堆越燒越旺,鼓聲與歌聲交織,影炎衛的舞姿愈發狂野,士兵們的歡呼震天。陳茂雄與曾秉豐並肩而立,一人如烈焰戰神,一人如暗夜魔王,酒壇碰撞,烈酒四濺,戰場的血腥與殺戮在這一刻化為勝利的狂歡。
杜那諾城的狂歡達到了頂點,火光映照著每張醉態可掬的臉龐,士兵們的歌聲與笑聲響徹夜空。陳茂雄舉起酒壇,高聲吼道:「為杜那諾!為勝利!」士兵們齊聲應和,聲浪如雷。曾秉豐靜靜站在一旁,魔刃「噬魂」斜靠身側,黑氣未散,卻在火光中顯得格外耀眼。他的目光掃過廣場,嘴角揚起一抹冷笑,低語道:「這只是開始。」
戰場的硝煙尚未散盡,男軍的戰意在遠方燃燒,但今晚,杜那諾城屬於勝者。陳茂雄與曾秉豐的對飲,成為這場狂歡的傳說,士兵們將這一刻銘記,歌頌著他們的無敵之姿。
狂歡過後,杜那諾城沉入一片詭譎的靜謐。廣場上,火盆的餘燼兀自燃燒,暗紅的火光搖曳,映照著地面上散落的酒盞與烤肉的殞骨,宛如一場血祭後的殞地。空氣中瀰漫著濃烈的酒氣,混雜著牛肉油脂的焦香與戰後殞骸的淡淡腥味,令人窒息。
遠處,幾名醉倒的士兵橫七豎八地躺在石板地上,低沉的鼾聲與偶爾的夢囈在夜色中飄蕩,像是戰場亡魂的低語。
城牆外的阿卡薩拉平原沉浸在無邊的黑暗中,唯有遠方的烽火殞地閃爍著微弱的紅光,彷彿戰爭的傷痕尚未癒合。夜風從平原吹來,帶著涼意與硝煙的氣息,捲起地面的塵土與殞骸碎片,發出細微的沙沙聲。天空無星,厚重的雲層低垂,壓得人喘不過氣,偶爾一道閃電劃破天際,照亮遠處斷裂的戰旗與散落的斷矛,隨即又陷入更深的黑暗。
曾秉豐獨自登上城樓,黑色長袍在夜風中翻飛,宛如暗夜中的幽靈。他的步伐沉穩,每一步踏在古老的石階上,都發出低沉的回響,彷彿與這座城的脈動共鳴。城樓頂端的瞭望台寒風凜冽,石欄上覆著一層薄霜,映著火盆的微光,閃爍著冷冽的光澤。他停下腳步,負手而立,長髮被風掀起,亂舞如蛇,露出那雙深邃如淵的眼眸,凝視著遠方的黑暗。他的魔刃「噬魂」斜靠在身旁,刀身隱隱嗡鳴,黑氣如絲,緩緩繞著刃緣流動,彷彿在低語戰場的血腥記憶。
身後,沉重的腳步聲打破了夜的寂靜。陳茂雄緩緩走來,暗灰戰袍半解,露出結實的胸膛與纏著止血布的肩頭,布條已被鮮血滲透,暗紅的血跡在火光下顯得觸目驚心。他的臉龐滿是塵土與血痕,卻掩不住眼中殞留的戰火餘熱,宛如一頭尚未熄滅怒焰的雄獅。他的法印手臂隱隱發光,橘紅的光芒在夜色中跳動,像是未完全平息的烈焰,與城樓下的火盆遙相呼應。
陳茂雄停下腳步,站在曾秉豐身側,雙手撐在石欄上,目光掃過平原的黑暗,低聲道:「今晚,我們贏得漂亮。」他的聲音粗獷,卻帶著一絲試探,彷彿試圖從這位魔王般的男人身上窺探出一絲真意。風捲起他的戰袍,布料拍打在石欄上,發出低沉的聲響,與遠處平原的風聲交織,像是戰場的殞魂在低吟。
曾秉豐沒有回頭,目光依舊鎖定遠方的黑暗,嘴角微微上揚,露出一抹冷冽的笑意。「贏,從來只是手段。」他的聲音低沉,帶著一種穿透夜色的寒意,像是從地獄深處傳來的低語。風吹過他的黑袍,袍角翻飛,隱隱露出腰間一枚古樸的玉佩,玉佩上刻著模糊的紋路,在火光下閃過一絲詭異的暗芒,隨即被袍角掩去。
陳茂雄沉默片刻,粗壯的手指輕敲石欄,發出沉悶的響聲。
他的目光從平原移到曾秉豐身上,眉頭微皺,終於壓低聲音,問道:「曾秉豐……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強大的?」他的語氣中帶著難以掩飾的疑惑,甚至有一絲不安。作為杜那諾軍的戰神,他與曾秉豐並肩作戰,深知這個人的聰明與狠絕,武藝更是出神入化,但今日的曾秉豐,卻以一己之力橫掃江俊毅、陳韋勳、何勝勳、劉永浤四大將星,震懾男軍十萬鐵騎,這種力量已遠超凡人之境,宛如神魔降世。
曾秉豐緩緩轉身,黑袍在夜風中獵獵作響,宛如一隻展開雙翼的黑鷹。他的臉龐在火光映照下半明半暗,左邊的輪廓被火光鍍上暖紅,右邊卻沉入陰影,顯得格外幽冷。他的雙眼泛起一絲幽暗的光芒,像是深淵中的星火,凝視著陳茂雄,彷彿要將對方的靈魂看穿。城樓下的火盆突然竄起一道火焰,火光映在他的眼中,宛如燃燒的魔焰,讓陳茂雄不由得心頭一緊。
「你想知道?」曾秉豐的聲音低沉而緩慢,每個字都像是從喉嚨深處擠出,帶著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壓迫感。他的嘴角緩緩勾起一抹意味深長的弧度,眼中閃過一絲複雜的情緒——似是嘲諷,似是追憶,又似是一種難以言喻的狂熱。
陳茂雄屏住呼吸,心跳聲在胸腔裡重重撞擊,彷彿連夜風都為之一滯。他緊盯著曾秉豐,等待著答案。遠處的平原上,一陣低沉的風聲捲過,帶起一陣細碎的沙塵,像是戰場殞魂的低語。城樓下的火盆微微搖曳,火光在石牆上投下扭曲的影子,彷彿在訴說某個未解的秘密。
曾秉豐的目光微微上移,彷彿穿透了夜幕,看向某個遙遠的所在。他的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卻帶著一種讓人無法忽視的魔力:「那一天,在——」
話音未落,一陣突如其來的狂風從平原捲來,夾雜著硝煙與血腥的氣息,吹滅了城樓下的一盞火盆,黑暗瞬間吞噬了半個瞭望台。曾秉豐的黑袍被風掀起,玉佩再次閃過一絲暗芒,宛如夜色中的鬼火。他的話語被風聲打斷,卻讓陳茂雄的心跳更加劇烈,彷彿即將觸及某個禁忌的真相。
ns216.73.216.82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