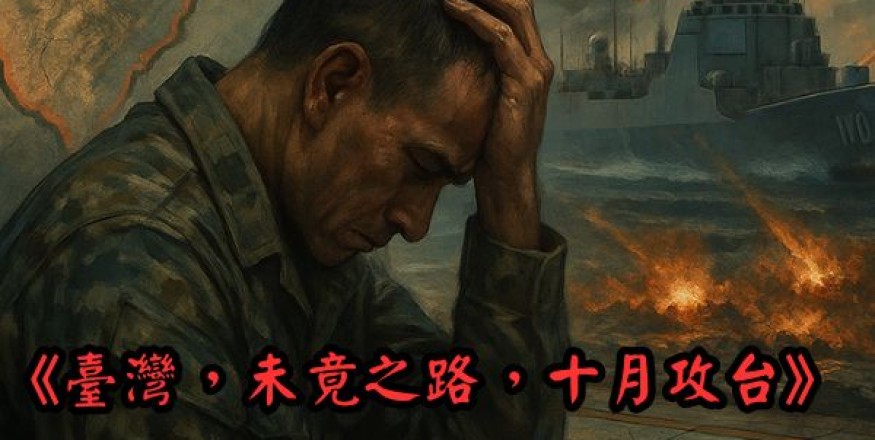風不曾停歇。
澎湖的天氣比往常還冷,灰色的雲壓著島嶼,一整日都像傍晚,沒有陽光,也沒有回音。第六日,補給艦仍未現身。中共艦隊封鎖島鏈,連空投都無法突破。島上所有資源進入戰時管制:彈藥限用,燃料僅供戰備車與重砲,抗生素與止痛針由營長親簽才可施打。醫務兵在臨時搭起的帆布醫棚裡,只剩碘酒與繃帶堆成山,濃烈的藥味掩不住血與膿,病號越來越多。
有的士兵因飢餓眼神渙散,有的則在鋪著保溫毯的床上昏迷,喃喃地喊著母親的名字。作戰日誌從每日簡報縮成一紙,最後甚至只剩下手寫數行:「仍守,無援。」
何翊瑞看著彈藥盤裡空倉一列列,沉默良久。他未下令收兵,也未通報中央「請求增援」——他明白,這世上最冷的,不是寒風,而是台北的沉默。整座澎湖,就是他背後的戰線。不能退,也無處可退。
午後,風裡傳來鍋碗瓢盆的碰撞聲。一列列百姓從村裡走來,推著腳踏車、扛著帆布袋、抬著破紙箱。裡頭是自家曬的米、自釀的鹹菜、祖傳的黑糖薑湯,有些甚至是原本要供年節用的米酒與糕點。他們神情凝重卻無畏,一步步朝營區走來。
「上校,你幫過我們……現在換我們了。」一位老農把布袋放下,手指僵硬得無法伸直,卻仍努力敬了一個軍禮。「你讓阿兵哥幫我們修水塔、送病人去診所、蓋雞舍……你是咱澎湖的好人。」
沒有鼓掌,沒有演講。就這樣,一袋米接著一袋米進了軍營,一碗薑湯、一片鹹菜,送到每一道戰壕。士兵們紅著眼、低著頭,把這些戰時恩情,一匙一匙吞進肚裡,不敢哭出聲,怕嚇壞送飯的孩子,也怕失去僅存的尊嚴。
「不要謝我們,」一位小學生舉著小竹籃,裡面是他母親蒸的一碗地瓜粥。「你們還沒走,我們才敢睡。」
這一夜,軍與民不再分彼此。寒夜裡的火盆圍著軍裝與便服;米酒與薑湯混在一起,成為唯一的熱源。他們彼此不談勝敗,只談明天是否還會有人來送飯,與島是否還在。
而台灣本島的新聞,像腐敗的刺,一根根刺進每個前線軍人的神經。「憲兵再兩週就沒飯吃了!」總統府副秘書長何志偉的發言在社群上引爆爭議。預算遭凍、軍餉難發、彈藥庫管制嚴重。國軍的飢餓不再只是隱喻,是血淋淋的事實。
評論區一片譏諷與懷疑:「要不要投降比較快?」「打不贏就別死撐。」甚至有人冷笑:「台灣能守幾天?美國真的會救?」
總統賴清德5月20日上任滿一周年。他在總統府發表演說,被問及兩岸議題時,重申:「只要對等尊嚴,台灣很樂意跟中國進行交流合作。」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隨即質疑他說與中國對等交流是「惺惺作態」,分析人士指出,台灣目前的政治動蕩正在分散國會的焦點,並削弱公眾信心。
那一夜,何翊瑞在指揮所裡翻閱軍情簡報,衛星回傳台海上浮動的黑影:一艘艘解放軍艦艇宛如封鎖線,層層壓近。從前在金門服役時,他見過夜裡突襲、濃霧中躍灘,如今的海圖更密、更近,也更無聲。
東引、烏坵通訊信號衰弱,只能偶爾收到一句「尚可守」。那是一種不說出口的絕望:外島成棄子,本島難自保。
他走出指揮所,看到士兵們正烤著地瓜,笑聲壓得很低,像怕驚動遠方的死亡。有人唱起軍歌《梅花》,歌聲顫抖卻溫暖。他忽然想起,許多年前,也是這樣的冬夜。他還是少尉,守在金門東岸防區。夜裡海霧濃得伸手不見五指,雷達回波裡浮現數艘解放軍艦影。就在眾人還在判讀信號時,他率先登上哨台。緊張得幾乎握不住槍的他,扣下扳機,把整個彈匣打光,沒有命中一槍,卻因為提早警示,讓防區全線進入戰備。
事後他才知道,那一輪槍響嚇退了敵軍的試探登陸,也讓他撿回一條命。老連長事後拍著他的肩,語氣溫和卻沉重:「槍不一定救你,兵心才會。」
這句話,他從沒忘記。尤其現在,在澎湖的風裡,那句話彷彿又從回憶中浮現,陪他度過這無望的第六夜。
如今,他帶兵守這最後的補給島,手中只剩一半口糧、兩日油料,無船可渡、無彈可換。但他沒有打算撤,這不是戰術選擇,而是倫理決斷。
他提筆,寫下遺書:「若本島已無意接我等,無論政爭為何、援助為何,本人誓與澎湖共存。此役若亡,請國人記得,曾有一群無名兵士,死於渴望被記住的地方。」
他將信交給通訊兵,封進防水袋裡,準備隨最後一架無人機試圖送往台南軍區。信飛不飛得出,他不再猜。
翌日清晨,寒流南下。澎湖依舊無雪,但冷得像是要凍住每個人的呼吸。百姓又來送糙米糕、米酒,並用棉被裹著孩子。
「他們晚上不敢睡,我們陪你們一起守。」一位母親說。
那一刻,戰地不再是軍營的一線,而是整座島嶼的每一戶人家、每一雙眼睛。他們站在歷史的最後一夜,不為勝利,不為救援,只為一種信仰——島雖小,心不降。
ns216.73.216.251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