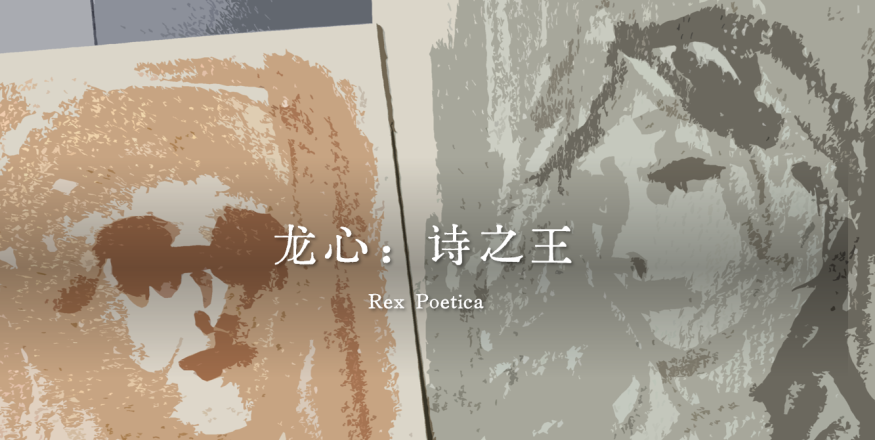Nothrop Frye(海英慈的讨伐)
教学楼藏在图书馆拐角后的花园里,沿一条极小的车道入内后,气息则由外界明朗一转为潮湿阴暗,由是不通风水学说,亦可对此处布局不利有些具身认知(la cognition incarnée)。与林懿文分开后,海英慈停在步道旁的花坛边观赏花铃饱满的毛地黄(Digitalis purpurea),校园林队为社区闻名的爱岗敬业团体,四月至后,各处花坛因填种郁金香,银叶莲和此种呈蓝紫,肉黄,嫩白的杯状花木而倍添新色。正值一二节课间,学生往来,海英慈蹲在花坛边,依次将三株花色不同的毛地黄花杯观察一遍,又查询其词源来去:其名来自‘手指’(digitus)一词语,内里又可提取洋地黄苷(digitoxin),有剧毒。
Digitalis。海英慈默念一遍,觉得这音节十分利落好听,复扶着背包起身,摇晃以寻平衡,向老旧而“风水欠佳,影响学生精气神”的老式教学楼去。多年过去,她的背包仍因时常容纳其感上课需用之杂物而变得过于沉重:一本法语词典,用于打发时间;一本《红楼梦》,用于打发《科林斯便携词典》变得无趣后的时间。一卷毛笔,一个素描本,一盒水彩颜料和一袋钢笔,再加上一个三百二十五页的笔记本和一个水杯,这书包足以让她在上楼时抓紧背带,而那本她始终拿走手上的真正主角——她自己写的小说——则被夹在腋下。
她走上三楼,沿着侧面封闭唯顶端有窗的走廊向前,再左拐,教室已在眼前,侧面的液晶日程表显示:“10:00-11:35:小说叙事理论”。
7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f4ZJj0cfnq
海英慈推门而入。研究生一年级下学期刚开始一月,先前下课五分钟便人满为患的教室在上课前十分钟仍颇见远离讲台的舒适座位,可见学习热情的消退。她找到教室背后的座位,放包落座。
邻座是个与海英慈友善的同学,叫林黎离,曾给她过柚子和巧克力,文静又和善。海英慈和她打过招呼,课程教授就入内了,两人不曾多言,林黎离唯小声同她说:
“你上次的pre做的真好。”
正此时,海英慈看见这门课程的授课老师,万玲仪教授露出笑容,用她极标准的英文开始同学生寒暄。万教授披一件羊毛外套,面色白皙红润,据说她应是八十年代初的大学生,但容貌似只见四十岁后半,年龄成谜。
“Thanks for the very passionate presentation last week. The presenter shows much of the critical ability in criticizing the Anatomy of Criticism by Nothrop Frye. However, since it is a theory course, I want to again, before starting our class, stress the purpose of reading literary theory. Why do we read literary theory ? Literary criticism is by no means normative or prescriptive, it does not command anyone to read in certain way, but instead to propose a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text, and so must approach the system critically. We do not have to read a text strictly according to a certain theory.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the intelligent effort you made in the process trying to understand it[1]……”
万玲仪教授道,而即使她的目光没有转向海英慈的方向而更像是看着教室后方的电子钟,海英慈已对她的下一句话的语言主体有了预感:
“It is not like, as some students may feel or propose that a theory is fixed or it is imposed, nor it will be totally WRONG. Every theory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whole knowledge system in expanding the literary commentary, thus, our understanding[2]……”
海英慈翻了个白眼。她打开手机,正欲发送消息,却看预想的联系人已发了信息给她。
“生日快乐!”
海英慈的另一个室友,因早出的作息先前不在宿舍的常桦给她发送了祝贺短信,此真诚的善意之举动引她微笑,先前欲发送的调侃类消息也就“入栈”滞后了。
“谢谢桦桦😊”
海英慈发送了一个可爱的表情包,并转而询问常桦想不想吃云南菜。
“好呀!”常桦回答。这个宿舍通常都在这样随性而顺滑的社交状态里,已成海英慈的一大安慰。台上,万玲仪教授仍在继续她的“为文学理论辩护(Defence for the Theory)”演讲,海英慈摇头,转头开始拿出她的上课工具包。海英慈从来很少听课,自上了研究生后,更是再没听过。每节课她都会准备一些特别的娱乐活动,画水彩,或者看书。经过了义务教育和大学的挫败后,她再也不在课上完成作业或企图自学了;上课是一个强制性的俱乐部时间。
“……你在做什么呢?”林黎离,因第一次坐在她身旁,倒是被她的阵仗吸引了,转头来看。海英慈正在翻开自己的小说,封面上用木浆纸糊着的标题处歪斜地用D公司的墨水,Red Dragon(红龙石),写着:“血圣女,vol3”。
“……看……看书。”海英慈犹豫道:“准确来说是批注一下,我想看看它的整体效果。”
海英慈不大擅长说话——起码不像她写作一样流畅,但两者之间必然存在松散的因果关系;她对经手的文字有种气质和文体上的要求,因此她多为犹豫,而干脆在生活中需要开口的时,用社交辞令快速结束,糊弄对话,不作真意。
“噢,这是你自己的书!”林黎离小声感叹:“这就是上次你在写的那本吗?——网上的好像被锁了,我看不见……”
“是的,我自己锁了……想避开一些人。”海英慈快速回答:“是的,我刚刚写完,所以想读读纸质版,看它的效果,我——”
我很期待这个过程;在写的时候,我不知道它最终连贯在一起的效果,这个整合的过程是最惊人的。海英慈心想,但她当然没有这么说。因为某些事,从上了研究生开始,她几乎不在任何地方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了,她咽下了那句话,听林黎离轻声感叹道:
“这么多!”她微笑,“好厉害啊。”
“厉害”,让海英慈有些不安,但同时,她又非常平和,坦然地接受了林黎离对她工作量的感慨:在同一个专业,林黎离知道写这么一本书,起码在绝对劳动量上意味着什么,而海英慈也不会多想。此事与成书内容无关,而单纯在于数量上,因此她不用担心,“能指所指不符”,或者题不对文。
“——我在读B大读研究生的时候喜欢读契诃夫的小说,但他写了很多短篇,我们是没法全部读完的,而我将这件事同一个研究结构主义的学姐说了,她告诉我,‘这些故事都是有套路的,有结构的啊’!——这就是我和结构主义的第一次相遇了,Fyre说的,其实也是这么一回事……”
台上,万教授仍在讲述文论的现实运用,而在提及“Fyre”这个名字时,海英慈彻底“绷不住”表情。课程已开始了十五分钟,此名依然未从主题褪去,她向林黎离感激地笑了笑,两人互相别开眼,就算结束了对话,她复拿起手机,开始和常桦发消息:
“她破防了。”
常桦似也对眼下场景有些忍俊不禁,亦回答:
“确实。”
海英慈摇头。万教授本科毕业于Z大,研究生和博士毕业于B大,附有多次国外旅学经验,学术成果颇丰,是系里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希望她担任导师的学生颇有十数,常桦本科就读于同一院校,提早就告诉过海英慈万教授的课十分“硬核”,可能会有收获,而海英慈,尽管面上礼貌地应答了,在看见万教授的瞬间,她就默默地别过了头。
知识分子。她心想。
海英慈不是什么知识分子,也基本,到了现在,理解了自己不喜欢知识分子。但她和万教授发生冲突的次数比她预想中多了一次:从零到一,而和万教授发生冲突的时间也比她早了许多:开学第一个月的末尾,海英慈已做完了她的第二个presentation,在万教授的课上,把Nothrop Frye的文学理论批得一文不值。
“——创作基于的是生活,是无限的,评论,若按照弗莱所说,基于创作的文本和脱胎于艺术本身的理论,则是有限的,以有限来评价无限,还声称评论将和创作有同等的地位,只有好的评论家才能评论,岂不是管中窥豹,欲以其一而格致无穷,而十分可笑吗?”
海英慈直接地说:“我在这里以一个极具文学天赋(也当然因此痛苦),几乎是天生就需要创作文学无论我是否以此作为职业的人的立场声明,在文学中,永远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系统性。最美的,最值得探索为之奋斗的事物埋藏在未知的混沌中。”
这个presentation持续了整整四十五分钟,因为选择了第一天做展示的只有海英慈和她的搭档。
在质询缓解,有一位男生问海英慈:“你认为你是个作家,而不需要文学理论,或者读者参与吗?”
海英慈没有停止过微笑。她的眼睛睁得很大,介乎孩子气和狰狞之间。在日常生活中,她非常“圆滑”;她像个没有野心和能动的青年,乳臭未干,愣头愣脑,但当她站在讲台上时,她统治着这个空间。
“No。”她回答:“I am a writer by my work.”
7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NyctIe2Duj
所有环节都结束后,万教授似乎被“惊吓”了,她在四十五分钟以后就认为这节课将结束,匆忙进行了点评,而经过提醒,则恍然醒悟还有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万教授胡乱地回答了“Fyre为何属于提倡批评和道德不割裂的一派”这个问题,但显然无人,包括她自己的逻辑在内,能明白这个回答为何是对的。因为那是错的。海英慈知道这个叫弗莱的文论家是一个根本不懂得何为创作,何为“文章憎命达”,何为“作家心血”的人,而一个忽视她人感受的人,不可能明白什么是道德。
到了最后,万教授流畅的英语已经破碎,她只能用中文开始解释。这也不让海英慈惊讶:海英慈已发现万教授流畅的阐释只能运用在她自己已拆解过的知识理论上,而对于她未知的部分,她照样需要磕绊。
“但她已经比张教授好了。”海英慈后来对常桦说:“她起码没有像那个老男人一样,对着质疑他的学生说,‘你退学,你回家吧’。”
海英慈不想说服任何人,她也不想向其余人证明什么事。她在课堂上“大发雷霆”,将Frye从头到尾批判一遍的原因只有:她不小心选了这本书做阅读,而这个文论家实在太不懂创作,以及,如果她给Frye留了任何颜面,都会给她自己增加工作量,同时给教授“挽尊”的机会。整个准备的过程并不愉快,像将一份难吃的食物细细嚼碎,她读得如此认真,乃至没有任何质疑者可以为Frye说一句好话。
但海英慈,尽管被说成“passionate”,在展示结束后,心情很冷漠。她只感在第一个月结束了这个作业是个正确的选择,以及,也许在这个时间节点,正式为“创作”做一个符合道义和现实的声明,是再合适不过的。
现在她已经不会想这么做了;她几乎“懒得”这么做。
海英慈低头,不例会万教授继续为理论辩护,而打开了她自己的书。她皱着眉,划出其中的错别字,又用钢笔描摹那气势如虹的句子,重新感受曾流淌过她脑海的音韵。
因为海英慈已经“写完”了。她已经彻底将她作为一个作者的证据和证明,无可置疑地握在了手中,而于此而来的,是一种莫大的,从未有过的安稳。她感到平静。
她戴上耳机,看完一章,又放下书,看了眼浏览器,而大约正是这“平静”的错,鬼差神使地,她点开了经常访问中的一个网页,查看其中的更新。
7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4XwOczTEq2
这是个蓝色的社交网络媒体,属于一个有紫色头像的人。海英慈下滑页面,数秒之后,面色复杂,欲言又止。
最顶的社交帖文上赫然写着:“祝你生日快乐,路路。无论你在哪,祝你一切都好。”
“果然。”海英慈忍不住想:“死性不改。”
而无论是课程的声音还是她心中的宁静都一扫而空。她在此感到一种激发(elevated)的状态,伴随那咬牙切齿的名字:
E。
7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94lech3k2n
[1] 感谢上周充满热情的展示。演讲者在批评诺思罗普·弗莱的《批评的剖析》时展现了很强的批判能力。不过,因为这是一门理论课程,我想在上课前再次强调我们阅读文学理论的目的。我们为什么要阅读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绝非规范性或规定性的,它并不要求人们以某种特定方式去阅读文本,而是提出一种理解文本的视角,因此我们也必须以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些理论体系。我们不必严格按照某一种理论去解读文本,更重要的是,在你努力理解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智慧与思考……
7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YoeI3Z8hly
[2] 这并不是像有些同学可能认为或提出的那样,理论是固定的,或是被强加的,也并不意味着某个理论就是完全“错误”的。每一种理论都是扩展文学评论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它也会拓展我们的理解。